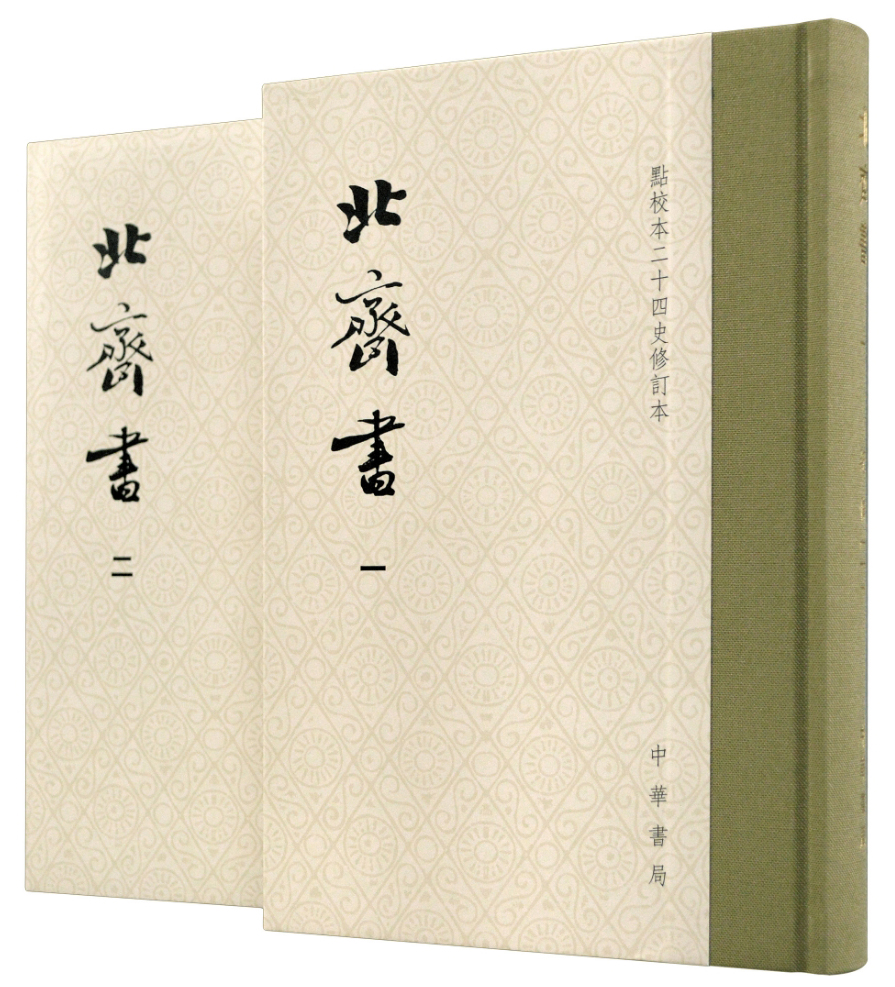
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《北齐书》
高欢两废皇帝,一逐其君,《北齐书·文宣(笔者按:即高洋,以下括弧中注释均为笔者所加,不一一注明)纪》“论曰”又说:“高祖(高欢)平定四胡(尔朱氏),威权延世,迁邺之后,虽主器有人,号令所加,政皆自出。”加上高欢死后,高洋随即禅代,高欢的历史形象很难不与曹、马相同。唐朱敬则论高欢临终兵败云:“昔魏祖(曹操)西征,中道不豫;晋景(司马师)南伐,回兵乃殂。此并业未半而意穷,功垂成而景促。是以留连末命,委曲临终,不可尽也。”宋胡寅也说:“宇文泰、高欢一时之杰,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志,而欢先得之。”“高欢身冒矢石,辛勤百战,变家为国。”皆为例证。据此“高欢奸臣说”已牢不可破,然而参照其他史籍,犹有发覆余地。《资治通鉴》就说高欢“自病逐君之丑,侍静帝礼甚恭,事无大小必以闻,可否听旨”,与《北齐书》之载截然相反。那么,何者才贴近史实呢?
北魏末期首位“挟天子”的强臣,并非高欢而是尔朱荣。尔朱荣在河阴变后,专擅政权,《魏书·尔朱荣传》说他“身虽居外,恒遥制朝廷”,这与《北齐书·孙腾、司马子如、高隆之传》“史臣曰”之高欢“以晋阳戎马之地,霸图攸属,治兵训旅,遥制朝权”完全一致。孝庄帝不满大权旁落,更担心尔朱荣会再次篡位,便将其置于死地;孝静帝却与高欢君臣始终,共治天下十三年。但孝静帝在高澄执政后,也走上孝庄帝的旧路,与荀济、元瑾等计划暗杀权臣。孝静帝前后的差异,似乎表明《资治通鉴》所述不假,高欢确实恭谨侍君至死,君臣才能各安其分。
能否因高欢奉君恭敬谨慎,就认定他忠于魏室呢?对当事人孝静帝来说,答案是肯定的。高欢“每侍宴,俯伏上寿”,孝静帝与之君臣相得。而高澄“尝侍饮,大举觞曰:‘臣澄劝陛下酒。’”孝静帝便不悦道:“自古无不亡之国,朕亦何用此活!”决意除之。孝静帝是东魏政权的代表,亲历高欢、高澄执政时期,连他都视高欢为魏室忠臣,后人又如何仅凭高洋禅代,便以“高欢奸臣说”为是呢?
高氏禅代遭遇的巨大困难也是“高欢奸臣说”的反证。高澄图谋易代,心腹陈元康却对魏收说:“观诸人语专欲误王,我向已启王。受朝命,置官僚,元康叨忝或得黄门郎,但时事未可耳。”即使高洋掌政,“时事”仍对禅代不利。高洋心腹高德政至邺都“讽喻公卿”,竟“莫有应者”,高洋到平都城,召诸勋将,告以禅让事,“诸将等忽闻,皆愕然”,也“莫敢答者”。就连高洋之母娄昭君亦对禅代不以为然,称:“汝父如龙,兄如虎,犹以天位不可妄据,终身北面,汝独何人,欲行舜、禹之事乎?”高欢若有代魏之想,高氏禅代应如曹氏、司马氏一般平顺才是,高洋却要与其母在内的“拥魏派”反复斗争,一度放弃,最后还是突发至邺都,逼孝静帝退位,才得践祚(拙文:《“人心思魏”与魏齐禅代》,《台大历史学报》第42期,21-34页)。高欢至死效忠魏室,未替子孙篡位铺路,又怎能将之与曹、马并论呢?
朱敬则、胡寅已看出高欢对君臣之伦的高度重视,朱敬则指高欢“废立虽多,不失臣节”,胡寅却认为:“孝武西奔,非欢逐之,而欢自以为丑,降心刻意,事静帝甚恭,君臣相安,十有余年,宇文泰惭德多矣。《易》曰:‘无咎者,善补过也。’高欢有焉。”他受《北齐书》之言及高洋代魏影响,视高欢为曹、马之流,也让所论前后龃龉。其实早在隋唐,高欢的历史形象即由忠转奸,也造成后人认识之讹。本文欲复原高欢事迹,考察其历史形象的改变,希冀能稍加修正成说。
一、高欢事迹的还原
高欢事迹主要保留在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北史》《资治通鉴》中,但这些记载却常相互矛盾。例如高欢在河阴之变中的表现就有两说,《魏书·尔朱荣传》称他力劝尔朱荣放弃篡位,随后更主张复迎孝庄帝;《周书·贺拔岳传》却说高欢劝尔朱荣登基。《资治通鉴》以《周书》之载为确,理由是“盖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神武(高欢)掩此恶,故云尔”。考虑到魏收《魏书》的秽史之称与高欢曾对魏收说“我后世身名在卿手,勿谓我不知”,《资治通鉴》的论断无疑有极大的说服力。但此论并未考虑《周书》依据的西魏北周文献材料本就对高欢抱持强烈敌意,其所录宇文泰讨伐高欢之檄文,罗列高欢五大罪状之一即劝尔朱荣称帝,而其余四项罪名:劝尔朱世隆返攻洛阳;说尔朱兆弑孝庄帝;弑后废帝、节闵帝二君,皆为刻意栽赃,则《周书·贺拔岳传》所言便难逃污蔑之嫌(拙文:《帝纪微言:〈魏书〉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》,《文史哲》2022年第1期,67页)。
高欢统领六镇余众,是发迹的第一步,此事诸书所载时间也有两说。以《北齐书·神武纪》为底本的《北史·齐神武纪》,称高欢是在平定纥豆陵步藩,成为尔朱兆心腹后,趁其酒醉之际,获得六镇之众的统帅权,不久更提议携镇民入山东就食。《魏书·尔朱兆传》《北齐书·慕容绍宗传》却说东出是尔朱兆原有的规划,委任高欢为冀州刺史,给予六镇鲜卑的统帅权,乃让高欢协助抗敌的条件。
吕思勉指六镇之民对尔朱氏统治心怀怨恨,不肯尽力应敌,故尔朱兆分兵高欢,乃情势所迫,不得不然,进而以《魏书·尔朱兆传》《北齐书·慕容绍宗传》之说为确(吕思勉:《两晋南北朝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版,538页)。廖基添以张保洛先随葛荣,后从尔朱兆,再“隶高祖为都督,从讨步藩”证实吕说(廖基添:《高欢建义史事考辨——对〈北齐书·神武纪〉的订正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21年第4期,60页),则高欢统率六镇镇民便在平纥豆陵步藩之前。
廖基添从高欢不出井陉至定州,而向西南绕路,出滏口往相州(邺城),认为尔朱兆为抢占尔朱世隆等控制的邺城才派高欢率众东出(廖基添:《高欢建义史事考辨——对〈北齐书·神武纪〉的订正》,61-66页)。但高欢此行若为夺取邺城,为何在自取邺郊车营租米后,即率军直抵信都(冀州)?可见冀州才是高欢一众的目的地。冀、定、瀛本有军府,于此安插降户乃北魏旧制,此前北魏就将六镇降户安置于冀、定、瀛之地(陈寅恪口述、万绳楠整理: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,云龙出版社,1995年版,304页)。为何是冀州而非其他两地呢?因冀州为河北大藩,物产富饶。考虑到尔朱兆入洛后不久,便派监军孙白鹞以征马为名赴冀,企图将高乾、高昂兄弟一网打尽;则尔朱兆早有让“大小二十六反,诛夷者半,犹草窃不止”的葛荣余众就食冀州之意。那么尔朱兆以冀州刺史为酬,使高欢协力抗敌,随后命其率众东进,不过依循既定方略而已。但此一人事案,仍须执政的尔朱世隆批准才能正式生效。尔朱世隆为拉拢高欢,普泰元年三月封他为勃海王,并征其入朝,在遭婉拒后,四月任命高欢为冀州刺史,也等于追认尔朱兆的全盘计划。
高欢起家的第二步,是与高乾兄弟合作,得到冀州根据地。薛海波认为:“高乾实际上是在尔朱氏和六镇降户的军事实力的压力下,做出向高欢让出冀州决策的。”(薛海波:《5-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20年版,292页)廖基添认同薛说,并据《关东风俗传》“献武(高欢)初在冀郡,大族起应之”,指出:“在高欢与高乾的政治结合中,高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,这不仅是实力所致,也是时势使然。”(廖基添:《高欢建义史事考辨——对〈北齐书·神武纪〉的订正》,70页)然而,高乾、高昂兄弟所部兵力,其实能与高欢一搏。高昂旗下的三千部曲“前后战斗,不减鲜卑”,若非高昂率千骑力战,高欢在韩陵之役早已败北。故高昂在得知高乾献出冀州后,会送高乾妇人布裙,讥笑其无胆。张金龙就认为:“当时高欢根本不具备‘扬声以讨乾’而使高乾部属‘众情惶惧’的实力。”(张金龙:《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》,《考古论史——张金龙学术论文集》,人民出版社,2019年版,284页)那么,高乾又为何会与高欢携手呢?
高乾为孝庄帝羽翼,高欢则是尔朱氏旗下的拥孝庄帝派,这是两人一拍即合的基础(拙文:《帝纪微言:〈魏书〉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》,68-69页),故而李元忠才会初见高欢就断定“高乾邕(高乾)兄弟必为明公主人”。此外,内外形势对尔朱氏政权不利也是重要因素,李元忠即对高欢说:“天下形势可见,明公犹欲事尔朱乎?”高乾、李元忠初遇高欢便将本州(冀州、殷州)相让,正是看到尔朱氏政权行将崩塌的迹象。李元忠更说:“冀、殷合,沧、瀛、幽、定自然弭从。”那么,当高欢一举反旗,河北诸大族蜂起景随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因此,并不是在河北大族群起支持的“时势”下,高欢才压倒高乾占据主导地位;而是高乾为击败尔朱氏,主动向高欢让出根据地与领导权。但高乾兄弟反对奉节闵帝(孝文帝兄弟之子)为君,这让高欢不得不放弃“清君(节闵帝)侧”之想,改推宗室疏属元朗为君。在击败尔朱氏后的立君大会上,高乾兄弟一派为捍卫孝庄帝的历史地位,以节闵帝为尔朱氏所立否定其正当性,高欢只能改立孝武帝(拙文:《帝纪微言:〈魏书〉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》,69-72页),也为往后的君相冲突埋下伏笔。
李煜东认为拥戴节闵帝与高欢一众的利益冲突,故高欢对废节闵帝“不得已”的表态,只是托词(李煜东:《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——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2022年第4期,177-178页)。但高欢在起兵不久,即推元朗为帝,节闵帝的君位早于此时便被否定。高欢在抵洛前却召开立君大会,提出要以“亲贤”为标准;而节闵帝能得到尔朱世隆等人的拥戴,正为“亲贤”之故。高欢若非为续拥节闵帝,又何以如此?
高欢放弃续拥节闵帝的初衷,随即提出“高祖不可无后”的标准,拥立孝武帝。在孝武帝入关后,又以“孝昌丧乱,国统中绝,神主靡依,昭穆失序。永安(孝庄帝[孝文帝兄弟之子])以孝文为伯考,永熙(孝武帝[孝文帝之孙])迁孝明(孝文帝之孙)于夹室,业丧祚短,职此之由”,立孝文帝曾孙孝静帝为君,也凸显他对孝文帝国统的重视。
李煜东以为高欢提出“高祖不可无后”,非为维护孝文帝的法统,而是“合理、稳妥地废除元恭(节闵帝)、元朗”(李煜东:《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——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》,191页),更认为高欢拥立孝文帝之孙孝静帝即位“与孝文帝无直接的关联”,乃“东魏要从‘国统’的宏观层面树立正统,而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皇帝”(李煜东:《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——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》,176-177页)。但如前述,高欢本欲续拥节闵帝,故“高祖不可无后”便非为废君而设。考虑到尔朱荣称孝文帝之孙孝明帝为“继体正君”,崔㥄替孝文帝之孙孝武帝所作即位大赦诏亦云“朕托体孝文”,则高欢在孝文帝子孙中择君,不过延续尔朱荣对孝文帝国统的推崇。再者,孝静帝为孝文帝曾孙而非李氏所说的孝文帝之孙,高欢若拥立孝文帝之孙为帝,新君就与孝明帝、孝武帝同辈,又如何让“昭穆有序”?帝室因孝明帝无后才“昭穆失序”,新君就必须是孝文帝的曾孙,并认孝明帝为父,那么清河王元亶就要和孝静帝断绝父子关系,元亶才会说:“天子无父,苟使儿立,不惜余生。”孝静帝入继大宗让“中绝”的孝文帝国统得以恢复,东魏因而“昭穆有序”,孝武帝建立的西魏却仍“昭穆失序”,也就是说高欢借孝文帝国统,提升东魏的正统性(拙文:《帝纪微言:〈魏书〉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》,74-75页)。又怎能说孝静帝的即位“与孝文帝无直接关联”呢?高欢接连拥孝文帝之孙及曾孙为君,而不立其他皇帝的后裔为帝,又为何不是“单独针对某一皇帝”呢?
孝武帝入关后,西魏被时人视为正统,故“挟天子”的宇文泰在政权初建时,即能“奉主上以从民望”“扶弘义以致英俊”“秉至公以伏雄杰”,对内压制先进,营造团结;对外让高欢陷入“人物流散,何以为国”的恐惧中(拙文:《“君臣大义”与东、西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》,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》第52期,15-47页)。此外,高欢拥立十一岁的孝静帝登基,也让时人认定他必将篡位,人心因此更加动荡。高欢为团结内部,高度尊奉孝静帝,孝静帝不仅有人事权、赦免权、军权,更有生杀予夺之权。东魏也由“主弱臣强”,走向“君臣一体”,高欢才能凝聚人心、稳固政权(拙文:《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》,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》第51期,6-26页)。
高欢临终前对段韶说:“吾昔与卿父,冒涉艰险,同奖王室,建此大功。”过世当天,更“拳拳于其君”向孝静帝上最后一启。可知高欢临死仍以魏室忠臣自诩,以为王室建功立业为傲。而对孝静帝来说,高欢也是魏室不贰功臣。他不仅为高欢服丧,赐与象征拱卫帝室的“献武”谥号,更亲送高欢灵柩出殡,使其成为北魏、东魏异姓大臣的第一人,高欢的葬礼可谓哀荣备至。
“高欢奸臣说”的另一依据是高欢并未还政,即使孝静帝给予高欢最高规格的葬礼,也可能是被迫为之,不能以此认定高欢忠于魏室。但在高欢“礼甚恭,事无大小必以闻,可否听旨”的情况下,君相实为一体,并无归政问题。是高澄在当政后,破坏“君臣一体”,孝静帝才觉大权旁落,才要置高澄于此地,企求“威权复归帝室”。那么高欢的“礼甚恭”与高澄的“礼不恭”,对孝静帝来说,即是忠奸之分,这从他亲送高欢灵柩而不及高澄也能为证(拙文:《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》,《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》第51期,33-34页)。
后人对周公、诸葛亮推崇至极,但对经历他们“摄政”的王者而言却非如此。成王亲政后对周公不谅解,周公为此一度奔楚。后主在诸葛亮死后,压制民间追思的声浪,不给他立庙。孝静帝的态度与成王、后主截然不同,又怎能以高欢未改变权力结构一点,便认定他为奸臣呢?
二、高欢历史形象的改换
高欢勠力补过、极其尊君,也让他盖棺时的历史评价甚至超过周公、诸葛亮,那《北齐书》又为何会有高欢大权独揽的说法呢?这与“拥齐派”魏收、“拥魏派”阳休之的“齐元”之争有关。
魏收因协助撰写篡位文书,在天保朝青云直上,官至太子太傅。高洋对《魏书》编纂亦全力支持,《魏书》成书后更严厉压制诋毁浪潮,也无怪魏收会为高洋之死“悲不自胜”了。高洋为何如此欣赏魏收呢?因其素被人“见轻”,代魏又遭遇晋阳勋贵、邺都文臣群起反对,连娄昭君对此亦不以为然,还举高欢为龙、高澄为虎(暗指高洋为犬猪)为例,驳斥禅代之议。故高洋即使称帝,仍缺乏人心所向的“天命”,魏收便是替高洋建构“天命”的关键人物。
魏收《孝静帝禅位诏书》云:“天下之大,将非魏有,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,克剪多难,重悬日月;更缀参辰,庙以扫除,国由再造,鸿勋巨业,无德而称。”所撰《奉册书》则曰:“齐献武王应期授手,凤举龙骧,举废极以立天,扶倾柱而镇地,剪灭黎毒,匡我坠历,有大德于魏室,被博利于苍生。”《中庸》:“诗曰:‘嘉乐君子,宪宪令德,宜民宜人,受禄于天,保佑命之,自天申之。’故大德者必受命。”那么魏收所作两文便有高欢因“鸿勋巨业”而有“德”,进而受“天命”,高洋承高欢之“德”及“天命”易代的用意。
魏收于天保八年(557)开始编修北齐国史,在《神武(高欢)本纪》创造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,将北齐元年定在高欢韩陵之役获胜那年,也就是视高欢为北齐“天命”的开创者,禅代文书的精神也从而载入史册。值得注意的是,高洋即使到在位最后一年(天保十年,559)仍深恐东魏复辟,为此大杀元氏三千人,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在天保八年问世正合高洋所需,也难怪高洋对魏收如此赏识呵护。
然而此说却在天统二年(566)后,遭遇阳休之的挑战。阳休之虽亦参与禅代文书仪注,此前却泄漏篡位消息,让高洋首次篡位铩羽而归,可见阳休之属于“拥魏派”。也因此,阳休之在北齐建政后被贬为骁骑将军,天保朝仕途浮浮沉沉,更一度外放三年之久。高洋死后,魏收涕泗横流,阳休之则面无戚容。杨愔问其缘故,阳休之云:“天保之世,魏侯(魏收)时遇甚深。鄙夫以众人见待,佞哀诈泣,实非本怀。”他对高洋的不满亦可想见。
阳休之主张以高洋即位为齐元之始(“天保之岁为齐元说”),意指北齐代东魏所据的“德”与“天命”与高欢无涉。这便有两种意涵:一是认为高洋有“德”、有“天命”践祚;另一则视高洋无“德”、无“天命”代魏。但众人所以力阻高洋篡位,正为其“德”不足,故为后说,阳休之在魏收死后,能“讽动内外”使朝廷从其议,也是一证。
魏收对阳休之极为轻视,阳休之在魏收死后奉命修改《魏书》,也为“寡才学,淹延岁时,竟不措手”,其史才可以想见。魏收却无法回应阳休之的质疑,不得不写信向李德林求教。
从李德林的回信,可知阳休之的论据乃高欢“身未居摄”及“书元年者,当时实录,非追书也”。李德林对第一点反驳云:“摄之与相,其义一也。故周公摄政,孔子曰:‘周公相成王’;魏武(曹操)相汉,曹植曰:‘如虞翼唐’。摄者专赏罚之名,古今事殊,不可以体为断。”对第二点则驳斥道:“大齐之兴,实由武帝(高欢),谦匿受命,岂直史也?……若欲高祖事事谦冲,即须号令皆推魏氏(孝静帝)。便是编魏年,纪魏事,此即魏末功臣之传,岂复皇朝帝纪者也。”
阳休之称高欢“身未居摄”,即指高欢“相”孝静帝,“谦匿”“事事谦冲”“号令皆推魏氏”,也就是《资治通鉴》之“侍静帝礼甚恭,事无大小必以闻,可否听旨”,则高洋称帝那年才是齐元之始,而非高欢执政期。李德林却把高欢的“相”解释成“摄”,高欢既和周公、曹操一般“身已居摄”,北齐国史《神武本纪》也就名符其实。可知李德林为强化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,凭空创造了“高欢摄政论”。
不仅“高欢摄政论”与事实不符,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亦然。对高欢来说,韩陵战胜的历史意义并非受“天命”,而是与勋贵“同奖王室”。即便高欢“有大德于魏室”,依娄昭君之说,他仍因“天位不可妄据”而“终身北面”。魏收对此心知肚明,他自武定二年(544)后与阳休之一同草拟“国家大事诏命、军国文词”,亲历君相共治。他个人又受高欢“后世身名”嘱托,却因替高洋构筑禅代理论,不在《魏书》立《齐献武王传》,而于北齐国史创《神武本纪》,还发明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为之张目,所为皆与高欢遗愿严重背离。这也是魏收无力应对阳休之挑战,及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在其死后,即被“天保之岁为齐元说”取代的另一个原因。
那么李德林为何敢妄肆窜改史实呢?魏收对李德林极为赏识,“延誉之言,无所不及”,更赠与“公辅”之字,示意必将提携,李德林力挺魏收也是必然,何况他从未涉足东魏官场,与禅代之事毫无关系,为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强词辩护,自无历史包袱。
阳休之虽让朝廷改采“天保之岁为齐元说”,北齐不久却被北周所灭,阳休之与李德林一同被召至长安,最终却是李德林及其子李百药掌握隋唐时期的北齐国史话语权。李百药《北齐书》是在李德林入隋所修三十八篇《齐史》的基础上扩展而成,其本纪第一即《神武纪》,正循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;其《文宣纪》《孙腾、司马子如、高隆之传》的“高欢摄政论”,亦遵李德林之言。可见在李德林撰写《齐史》时,即已从经“高欢摄政论”强化后的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了。结合《周书》对高欢的百般诬陷,则在李百药、令狐德棻,东、西两系史官联手“按之入地”下,高欢在正史中的形象便已是“威福自己”“伺我神器”的曹、马之辈了。纵使《资治通鉴》保留高欢恭谦侍君之载,后人也很难不以“高欢奸臣说”为是。
李德林违背北齐末朝议,重拾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,更不惜污蔑、抹黑高欢,还有深刻的时代因素。北齐承袭东魏,正统性本不如继自西魏的北周,若依“天保之岁为齐元说”,北齐乃无“德”、无“天命”的高洋所建,最终被北周所灭,更是顺天应人,李德林等北齐旧臣在关中又何以自处?唯从“高欢摄政论”强化后的“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”,认定高欢以功业有“德”受“天命”而“身已居摄”,高洋承高欢之“德”与“天命”禅代,北齐在历史上才能与北周争对等,李德林等也可借以释怀。那么李德林此举就不只为报魏收恩遇,亦含对故国的眷恋。
“拥齐派”魏收与“拥魏派”阳休之掀起的“齐元”之争,从557年至636年,绵延八十载(拙文:《“齐元”之争与“高祖”更易:高欢、高洋历史地位的改换》,《汉学研究》第38卷第2期,128-130页)。“拥魏派”一度夺取主导权,却因北齐灭亡,让“拥齐派”获得最终胜利,伴随《周书》对高欢的丑化,高欢的历史形象遂由忠转奸,回响千年,迄今不绝。

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