距离上一次去那家羊肉面馆吃面,已经138天了。
面馆保底开了十几年,嵌在一排喧嚣的店面之间,尤其低眉敛目,几乎找不到存在感。好几年前,我住在它隔壁的小区,偶然间饿急来吃碗面,吃完便把它加进了“想不出要吃啥时的保险之选”清单。
后来我搬到别处,来得反而多了。这家小馆子不仅出品稳定,其他好处也不少:不用排队,没有选择困难。更重要的是,老板和店员就那两三位,一个利索的阿姨,一个宝相庄严的光头胖大叔,还有个从未露面的厨师。他们对新老食客一律不寒暄不交谈。如此种种,可真的太令人感到稳妥且轻松了。
这家店其实人气十足。尽管门头简陋窄小,里面却有包间,还有二楼,长期坐满各路大汉,就着滚烫的面条和羊肉锅仔大声嘎讪胡(上海话,闲聊)。我旁听过成吉思汗征服欧亚大陆,单飞程序员和产品经理谋划另起炉灶创业,事业单位里的人心拿捏之术,还见过情侣分手。
老板跟乔布斯似的,面相身形皆清癯,长期穿一件深色半高领打底衫,在门口的小工作间沉默切肉。顾客就着工作间玻璃上的菜单说出要吃什么,由老板转头向厨房用方言喊一声,短短几分钟后,面就上桌了。多年来,我都只让老板喊同一句:“白切——面,烂一点——”
我对这种几近凝固了的状态极为满意。如果生活本身动荡,那么我们总要夯点堡垒出来,作为安全感的来源。生活不过三餐一宿,吃住问题上要是稳妥了,舒适度就会高很多。有一群熟面孔总是站在原地,给人端上一碗不错的面,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安心的。为此,我几乎像献宝一样把这家店安利给朋友们,轮番带他们来吃。
但危险还是猝不及防降临了。有天加完班,我带着能吞下一头牛的胃跑过来,发现那个瑟缩的门面竟然上了锁。我也顾不得打破内心的平衡,迅速在地图软件上找了店家手机号打过去,那头冷漠地说:“暂时不开。”
我瞬间失去主张。过了这个面店,马路那头堪称美食荒漠,越走越积攒委屈。此情此景,让人觉得自己像是猝然被遗弃的怨妇,几乎可以在马路中央嚎啕出声。
店家说大概八月中旬再开,临近中旬,忍不住偶尔绕路去看看,门还是关着,越等越痴缠。等它终于重新开张,我趁点餐时发了牢骚:“怎么那么久不开?”老板还是一张冷脸:“我们去度假了,每年都是这样。”
原来我那么多年都无意识地避开了它打烊的时间,这简直令人有些得意了。在得知它的例行度假安排后,我便特别留意——但问题偏偏出在这里,它度假的时间越来越不固定。最近一两年吃的闭门羹次数之多,已经让我渐渐力乏,要爱不动了。
上一次去吃面,也是好不容易等到开张。例行把羊肉蘸到酱油碟里,一口下去我又忍不住:“老板,酱油换了吗?”他没有正面回答,只是问:“淡了吗?”表情语气都不如以往冷冽,听起来三分狡辩三分无力。
于是,那碗面我吃得很不得劲,和以往将汤面上的青蒜一一打捞干净也不影响心情的热切完全不同。店里也没人讲大人物的伟业和小人物的创业,另一桌坐着个和我同样形单影只的食客,佝偻着看手机。老板从工作间走出来,坐到门口抽烟。我发现他站在里头切肉时挺拔精神,简直有几分赵寅成的风采,但站在门口就是个干巴小老头。啊,真令人伤心。我决定跟这家店分手,立刻马上。
此后几日,我几乎天天经过这家店,它也日日都开着。倒是旁边原本很富贵的牛蛙店似乎关张了,让这条街像豁了颗门牙,于是亮着灯的面馆反而醒目了一点。原本长期在门后切肉的老板,变成了长期坐在门口抽烟,越看越是个无精打采的小老头。
我回想那些年慰藉肚肠的暖意,好几次想下车去吃碗面,但转念就打了退堂鼓。就像于心有愧的渣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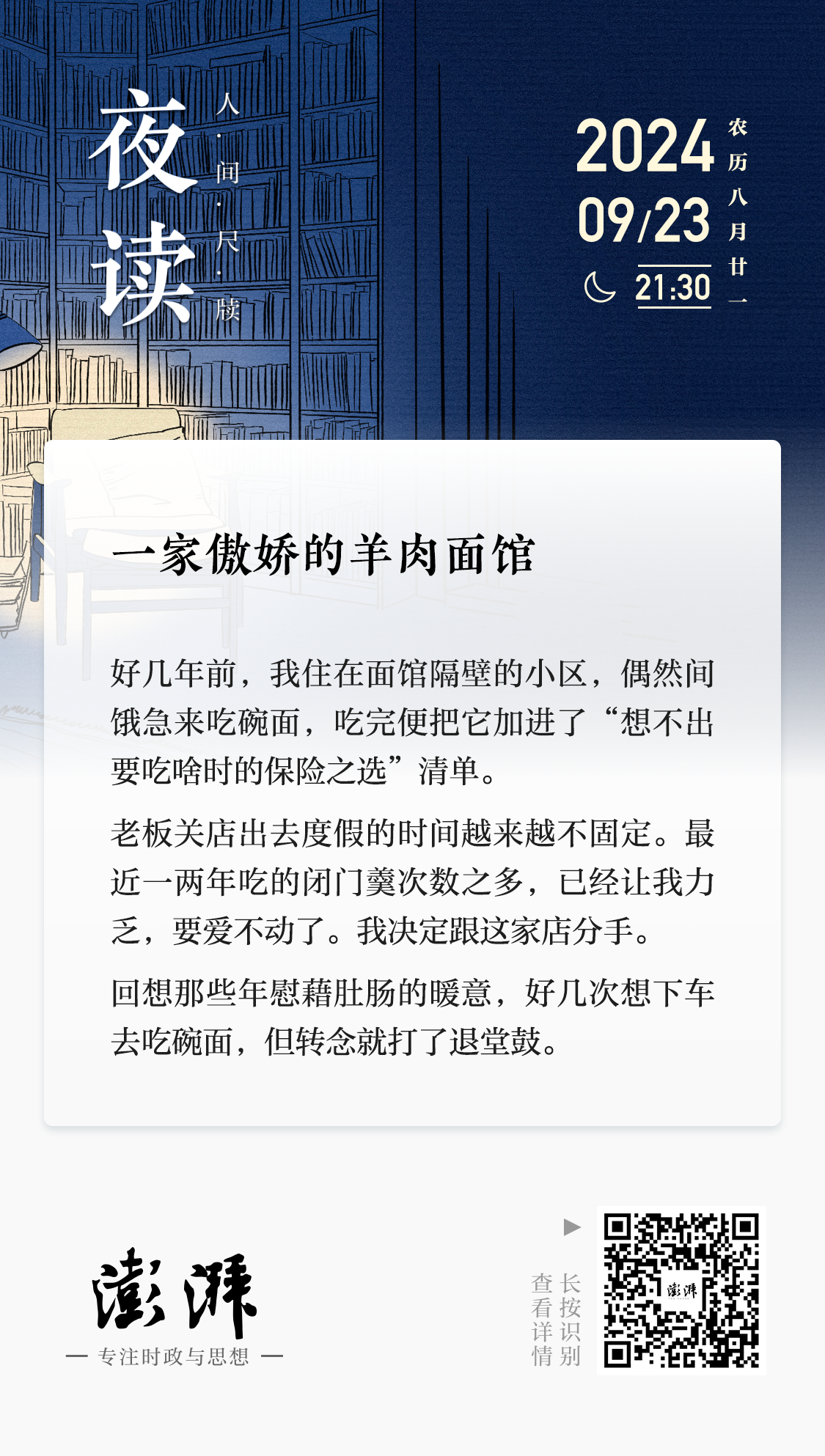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